前段时间,和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们互相问到了一个问题:“如果有个机会,能够选择让自己从未诞生,也因此不会经历世界上的一切,你会怎么选?”
我没有任何犹豫地选择了“我宁愿从未诞生”,而他们则感到十分惊讶——反之亦然,他们的惊讶本身也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就在十几分钟之前,我还在听大家讨论这世界上存在的种种问题:社会不公、经济不振、人际关系……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地方,对大部分人来说,如今大概并非一个特别宜居的地方,但他们竟然还是一边受着折磨,一边高兴地在这里继续待下去。
在这种时刻,很难不去引用两句在我心中(竟然)几乎同等重要的话。第一句来自加缪,早就非常出名:“真正严肃的哲学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判断生命值不值得活,就等于回答了哲学最基础的问题。”第二句则来自我最喜欢的游戏之一,VA-11 HALL-A:Cyberpunk Bartender Action,里面的一杯酒(Bad Touch)的简介:“我们毕竟不过是群哺乳动物。”前者让我们意识到“人生的意义”的紧迫性,而后者提醒着我们(可能)的本质。

图1: "We're nothing but mammals after all."
比起人类,我在外出散步时更喜欢盯着经过的狗看,因为它们也许比它们的主人更能揭示我们自己究竟是谁。巴甫洛夫、斯金纳,还有如今大多数的科学训犬指南都把犬类当作十分标准的条件反射机器,认为它们只是遵循动物的本能,对各种刺激作出反应,形成行为模式。
然而,行为主义不再如日中天的今天,我还是时常提醒着自己身为动物的本质。上面这一段描述,并不意味着人类就有多么的超然,恰恰相反,如果只是因为大脑被认为是我们思想的主体而忽略了我们的动物性,那么很多问题就将变得格外丑陋,因为我们将不得不使用各种借口去解释本来很清楚明晰的事情。关于这一点,巴塔耶就直接使用了“动物性”(l'animalité)这个词来表述——有这样一种矛盾,那就是我们的“人性”来自对“动物性”的否定,但却又始终处于想要回归“动物性”的冲动之中。(他对“动物性”以及相关的三层世界的定义,虽然出发点不同,但最终似乎与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的分层方式如出一辙。)
关于动物性,虽然看起来可能离题万里,但我还是想先转到另一个话题上去:生育。
更久之前,还和另几位朋友聊到了关于繁衍后代的事情:“你想要一个孩子吗?为什么?”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无需思考的问题,因此当然也不牵涉任何伦理思考——如果你硬要去问的话,他们可能会两手一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或者干脆反过来问你:“那又有什么不要孩子的理由呢?”
我并非是经受过严格训练的哲学家,但在关于生育的问题上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些想法。直到如今,我依然无法绕过几个重要的困惑,因而无法认同把“应该有一个后代”这件事作为默认选项这件事。
比如说,既然新生儿不可能在出生前就自由地作出“我想要被生下来/我想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种选择,那么繁衍这件事就必然是身为(准)父母替另一个人作出的选择。可是,这种选择的责任到底有多大,又是否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标准来帮助作出这个选择呢?看起来很多人并没有深入思考过这件事。
对很多父母和准父母来说,他们作出这个选择本质上是极为自私的。
当我在谷歌上搜索和这个问题相关的信息时,看到了许多在搜索结果上名列前茅的诸如“你应该有孩子的25个理由”之类的网页,而里面的那些理由不外乎“成为父母可以让你重燃激情”、“你的大多数朋友都会有孩子”、“你会在这个过程中成为更好的人”这样的理由,而在其他一些人现身说法的文本中,他们则大多数都强调了“感受到和孩子之间的爱”是多么的重要……但是,所有这些理由都是关于他们自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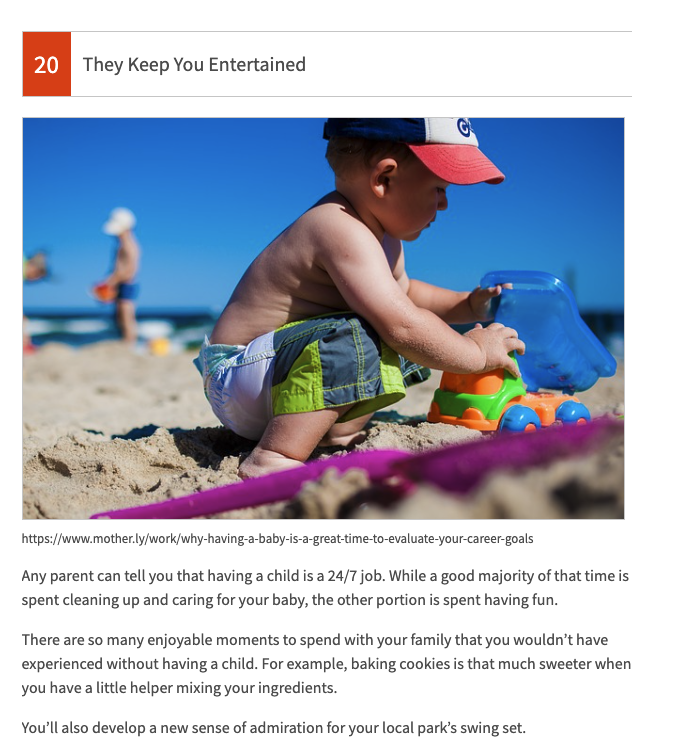
图2:"They Keep You Entertained"
也正因如此,当我听到别人说他们想要孩子的原因之一是“父母想要抱孙子”的时候,我会很想向他们脸上打一拳:因为他们不仅自私,还会在几十年后也变成和他们父母一样的人,逼迫自己的孩子再去生孩子,来满足他们自私的愿望。
当然,还有些人的理由是看似无私的:“人类保持生育是为了整个种群/基因的存续”。但这依然充满了傲慢,不仅把后代当成了基因版的地图涂色游戏的工具,还默认人类,或者人类中的某一个特定子集是“值得”存续下去的。可是,给地球造成大量污染的是人类,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其他种群造成了最多死亡、灭绝和伦理惨剧的也是人类,即使不说人类是比其他物种更糟糕的存在,我也很难得出人比狗在道义上更有资格存在下去的结论。
对于上面提到的这些人来说,孩子变成了手段,而不是目的。而且,把孩子作为生活的目的,很可能也是站不住脚的。Robert Solomon在他的那本简明哲学导论中对此有过一段简短的讨论:如果生活的意义不在于我们自己,而在于他人(比如我们的孩子),那么什么才能使他们的生活有意义呢?——难道无限以此类推下去,是他们的孩子吗?
问题总是存在,而有些人则选择换个方向——如果,我们替未出世的孩子们做出选择,是因为我们无私地相信这是对他们好呢?
当然,这首先还是无法避免“你凭什么可以替另一个人做决定”这种伦理问题,其次,“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比从未活过更好”似乎也并不是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比如,至少对我来说就是这样。每当我想到也许未来某天我可能会面临是否要有一个孩子的选择时,我都会忍不住问自己:这个世界真的很好吗?它需要好到什么程度,我才可以充满信心地自作主张,拉另一个人来到这里吗?
至少从过去几年看来,我本就不多的信心正日趋消磨,而我猜许多思考这个问题的其他人也有类似的想法。出生不是加入一个微信群聊,退出在大多数时候几乎都不是一个选项,那么拉另一个人加入就非得有比现在充足得多的理由才行。
(顺带一提,因为我的生理性别是男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有着更大的不自信:繁衍的大部分代价,无论是生理上的还是社会上的,都不是由我承担,这样的话,我又有什么资格去作出这种决定呢?)
当试图诉诸理性的路崎岖不平时,也许还有第三条路,一条可能许多人不愿主动承认,但又其实在许多观点中隐约透露出的路:人们生育,是因为亿万年来进化的构造让他们想要这样做,也让社会形成了一个鼓励他们这样做的结构。
我并不是一个自然决定论者,所以这段话并不意味着我认为人们必然天生倾向于制造后代,但我确实相信,在长期的进化中,激素分泌等发生在个体上的生理进程,让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衍生出了诸如社会结构等超越个体和生理的事物,并且最终成长到了七十七亿这样的量级。它的逻辑有点像学医药化学的室友给我讲解过的“脑—肠轴线”:许多看起来是精神层面的变化,实际上竟然是肠道内菌群作用的结果。
对于唯物主义者来说,这是几乎不需要去适应的逻辑,但现在的许多人似乎进入了某种新的二元论视角,将大脑和身体分开来看。我自己也曾或多或少有这样的倾向,以至于前一阵子读《Make Time》的时候,看到作者提示“不要把身体只看作运输你的大脑的交通工具”,突然意识到这其实正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容易遇到的盲区,也就是试图为非理性的行为寻找一个理性的缘由。
甚至,实际上所谓的“理性”在我们的行为中所占的比重,也可能因为我们的自负而受到了高估,就像我们倾向于严重高估自身记忆的准确程度一样。
人类(在很大程度上)是情绪动物,而情绪是我们动物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曾经非常有效地帮助人类在严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想想看,如果没有杏仁核的“战或逃”反应,可能我们身披兽皮的祖先已经因为傻站在野兽面前而变成盘中餐了),但如今的问题是现代生活的结构已经与我们的进化进程脱节(这也是如今许多人正关注的一个问题),以至于让它在许多时候显得不合时宜,像是人类一些退化后的器官一样。
从私人体验来说,我其实常常会有身体与内心脱节的感受,仿佛我的身体是自己内心的囚笼(前文提到的二元论视角),甚至是囚笼和狱卒、拷问者的综合——它不仅让我的思考受限,还用各种动物性的波动来干扰、甚至欺骗它。更进一步,即便如此,我的大脑还不得不想办法去满足它的各种需求,以避免自己和身体一起陷入衰弱、病痛,甚至毁灭。像这样分别去看,显然并不是一个能够与自己存在的有限性和解的方式。
正因如此,有时我会忍不住想:动物性到底是我们的本质、宿命与终点,还是一个应该像达尔文点一样不断收缩,最终革除存在的残余物?(当然,我也可以像住在丛林中的德鲁伊那样,声称重要的是保持“兽性”和“神性”的平衡,但这种论调很可能没有实际意义。)而无论倾向前者还是后者,我们都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思考那些并不愉快的问题:我们究竟是什么?而文明、理性、智慧……这些在语言中被构建为我们得以比地球上其他的动物更优秀的、几乎是人类独有的事物,又究竟意味着什么?
为了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有更多问题会衍生而出,更多的答案需要被考虑,而这些答案很可能也会永远处于一个临时性的状态里。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许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回望自己作为人的状态,重访我们的黑暗之心。